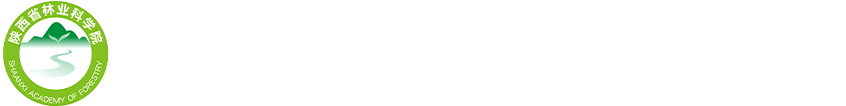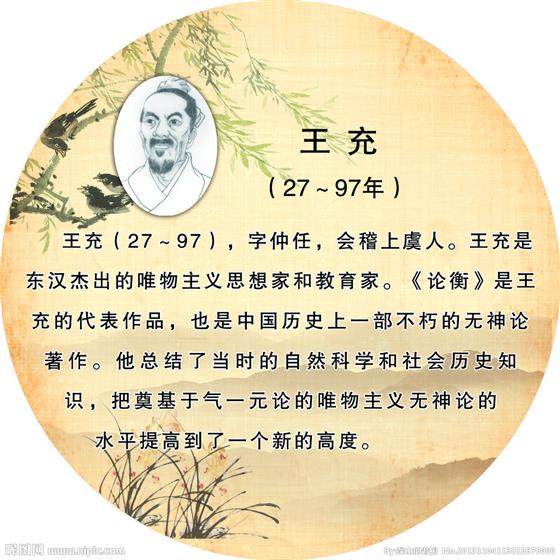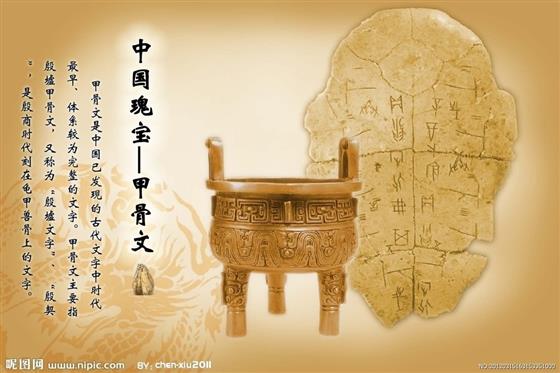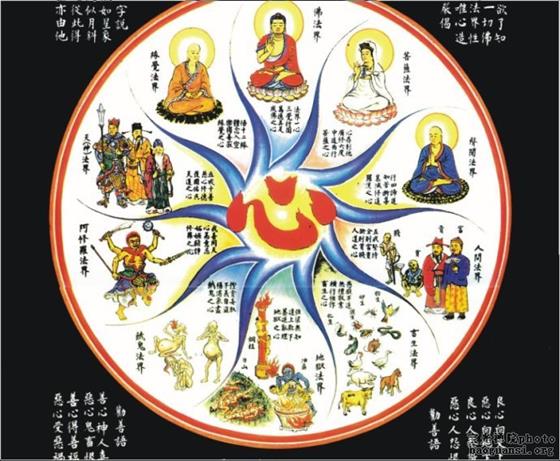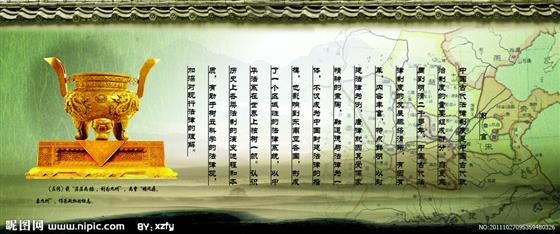秦羚学者
|
《说文》解释:“灋:刑也。平之如水,从水;廌,所以触不直者,去之,从去。法,今文省。”一般认为,法字中的三点水,表示法律、法度公平如水的表面;廌(zhì)即解廌、獬豸,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,能辨别是非曲直,在审理案件时,它能用角去触理曲的人。 许慎在《说文》中关于“法”的解释,大概来自王充。王充是汉代道家,但他的思想与先秦老庄思想、汉初“黄老之学”有所不同。王充的代表作《论衡》,是一部不朽的无神论传世之作。因王充擅长辩论,虽然结论实在,而论证却甚是诡异。在《论衡·是应》中他写道:“廌者,一角之羊也,情知有罪,皋陶治狱,其罪疑者,令羊触之。有罪则触,无罪则不触,斯盖天生一角圣兽,助狱为验。”相信科学的今天,人们一定知道,世间并无这种叫“廌”,似羊非羊,似鹿非鹿,似马非马,似牛非牛,也有人说与麒麟相像的“一角圣兽”。 经过许慎的《说文》注解,王充的说法被固定了下来。再晚一些时间,在王充和许慎说的基础上,《异物志》进一步说:“东北荒中,有兽名獬,一角,性忠,见人斗,则触不直者;闻人论,则咋不正者。”似乎更加神乎其神,甚至有些耸人听闻了。毫无疑问,这种说法“立意不错”,主观愿望很好,但有望文生义,妄加臆造之嫌,且它远离了法的本质,远离了法的本来面目,并为后世法学带来了诸多困惑,甚至将中国法治引入歧途。至于后来,有人硬是将“法”视为“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”,实在是混淆了“法”和“律”的区别。必须指出,今日中国之法治不彰,与上述“误解”和“混淆”被写进神圣的教科书不无关系! 下面,让我们从汉字造字学角度,看看“法的本质”。在甲骨文中,尚未发现“法”字。在金文中,“法”由左右两大部分三大块组成。第一块是左半部分的上面,即“去”(在甲骨文中,“去”为上下结构,是摆臂的人形+村邑的方框。今文“去”与“走”上半部均为“土”,在古文字中均是摆臂的人形),表示离开住地,代表为生存所进行的各种生产、社会活动;第二块是左半部分的下面,即“水”,像是柔软、流动的水体,代表无所抗拒而又无坚不克的物质;右半部分,也是第三大块,即“廌”,像是步态轻盈灵巧的麋鹿一类动物(注意,并非不伦不类的“独角兽”,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“鹿”,也可以将其理解为“马”。还记得“指鹿为马”的故事吗?单从字型看,“廌”的上半部分是“鹿”,下半部分是“马”),表示在野外活动的人,从水体流动和麋鹿一类动物的自由灵巧中,领悟到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存之道。有的金文,调整了法字的结构,突出了代表自然的“水”和“廌”。 再往后,篆文中的法字,基本承续金文字形,只是将左右结构调整成上下结构,上半部分是“水”加“廌”,下半部分是“去”。在篆文异体字中,已经出现了简化的“法”字,即在部件上省去了“廌”,这也使“法”字定型化。所以省略了“廌”,大概是说“廌”与“水”均指自然本真,这恰如道家信奉“上善若水”,水的特质代表了自然本真,用“水”完全可以代替“廌”。如果按照王充《论衡》和许慎《说文》对“廌”的解释,“廌”是“法”的核心构建,若将其省略,岂不令人匪夷所思?在先秦道家思想中,“道”代表了宇宙万物和谐运行的本质规律;“法”代表了天人合一、顺其自然的最高行事准则。以此观之,“法”字的造字本义是:人类从水、鹿等自然现象中领悟并践行生存之道,即“法”是暗合了宇宙万物的本质精神、天人合一、顺其自然的最高行事准则。这或许是“法”字的本源意义。 自然而然,自然界千变万化,无穷无尽。可以这样说,自然界唯一不变的,就是无穷演进、无穷变化,永不停歇。如此,暗合自然,顺其自然,天人合一的“法”,该当如何?答案必然是:“法”随变化了的自然而变化。也就是说,“法”是最高行事准则,其生命力在于顺其自然、因变而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变法”一词,自当无立足之地。如此嬗变的“法”,又当如何把握得住?这就得请出“律”字来,是“律”将“法”定位定量。 古人对“律”,也有不少解释。《尔雅•释诂》:“律,法也。”这似乎模糊了律与法的区别。《说文》:“律,均布也。”似乎是说,“律”是均衡广布于万物之中的真谛。这两部权威著作,并没有抓住“律的本质”。从字型看,“律”字,左右结构,由“彳(chì)”和聿(yù)组成。“彳”是街道、行路,“聿”是“筆”的本字。甲骨文中已经发现“律”字,与现在的结构基本相同。“律”字本义即书写在册的行事准则,也即写入法典、供人们处事遵行的条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所有的“律”都是书写出来的“法”,也是成文了的“法”。但从“法”的嬗变性来讲,所有的“律”都不是“法”本身,而是过了时的“法”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变法”的本质是“变律”,让“律条”变化跟上“法道”变化的步伐。“法”变了而“律”不变,必然违反自然,有碍进步!“律”与“法”存在天然的“时间差”,这个法律“时间差”只能缩小不能消除。历史上的争斗,大部分原因是为了“变律”,以缩小“法”与“律”的“时间差”。 经常与“法”字搭配的,还有一个“规”字。“规”字由“夫”和“见”两部分组成。甲骨文中,“夫”字也是两个字组成,即“大”加“一”。“大”表示成人,“一”是指事符号,代表发簪。“夫”的造字本义是用发簪束发的男子。古人认为,父母所赐须发不可剪除,成年男子需要用发簪束发,因而也是成年的标志。甲骨文中,见字也是两部分组成,即上半部的“目”,下半部的人。“见”的本义是“睁着眼睛看”。向前看为“见”,回头看为“艮”。“规”将“夫”与“见”组合在一起,造字本义是初涉社会的后生专注学习,用心观摩。很有意思,古人将圆之标准称为“规”,将方之标准称为“矩”。后来,本义消失,引伸出一些列新意,比如谋划、标准、范式、劝说等。“规”与“法”组合,自然是用“规”将“法”固定化的意思。“规”和“律”都是用来固定“法”,因此“规律”也叫“法则”。它体现着事物、现象和过程内在的、本质的必然的联系。 与“规”字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“章”字。没有见到甲骨文中的“章”字,金文中“章”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,上半部是“辛”,即“带木柄刺刀”,下半部是“田”,表示纵横刻画的圆圈标识,即在玉或石头局部刻画图文。“章”字本义即“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”。可见,“章”的具体明示作用显而易见。好像是“踏石留印”一般。如果说“律”是将“法”书写在纸上,是条文化,“章”则是将“法”落实到具体行动中。“章法”是行动中的“法”。 (责任编辑:admin) |